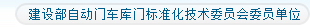|
|
|
|
| 传真:0512-66654828 |
|
| 邮箱:hanmadg@sina.com |
|
| 地址:苏州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278号 |
|
| 联系人:潘经理 13606139735 |
|
 |
|
|
|
|
| |
|
|
| |
清明忆故人
|
|
小时候清明是一个很平常的节日,并没有格外的欢喜或悲伤。原因在于没有特别好吃的,而我旧时对一切节日的情感,几乎都建立在“吃”的基础上。这一天我们必做的事是插杨柳,水塘边折了杨柳枝插下去,很容易成活。乡里杨柳都不是垂柳,枝条较硬较短,先向上空伸展,末梢才款款下垂。虽然现在看来,它比垂柳更有一种与乡间相衬的朴素,那时却太想要一棵自己的垂柳了。我们相信倒插杨柳长成后便是垂柳,也曾挑过一两枝粗细合中的枝子,将它倒插,后来往往忘了去验明,但这实验大抵是失败,水塘边仍是没有一棵垂柳。我们对垂柳的向往之情并不因此消失,有一回春天,在村头赵家屋边的空地篱笆旁,发现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柳树,枝条望去比一般柳枝柔软修长,便认定那是垂柳,几人扑上去攀折,把一棵小树拽得七零八落。废名的《桥》里,清明那一天细竹为小孩子打杨柳球,我很喜欢看。折一条长长的壮柳枝,将皮叶都一气捋到顶端,成一个绿球,执在手里,想必是袅袅好看的。我们只偶尔用柳枝编环,就平常得多了。
清明里我们给爷爷上坟,爷爷的坟在大坝山头的小坡上,离家两里路,就在三姑父家门前几十步。我记忆的最初片断,便是与爷爷有关的冬天。我和妹妹是家中第四第五个女儿,况且一出生便是两个,在期望得一个孙子的长辈心里,引来的巨大失落自不用说。从小我们得过许多来自奶奶和外公的脸色,爷爷却很喜欢我们,据父亲的说法,那是因为爷爷生病以后,发现他其实很孝顺,后悔从前对他的种种,转而喜欢起我们。父亲出生三个月便失怙,爷爷是他的继父,年轻时曾很暴躁,把他从学校打回来,让他去捡猪屎挣工分。我记忆所及时,爷爷大约已经生病,冬天的早晨在锅洞里焐熟了两个山芋,搬了大板凳到我们厨房外向阳的墙边坐着,一面喊:“大燕小燕,出来吃山芋!”他很喜欢吃山芋。太阳照得墙和山芋都黄黄的。然后便是爷爷的去世,大约在过年后,已经病得很沉重,一屋子的人守了一天,情况似乎又渐好转,父亲便背着我们往三姑父家吃晚饭。正吃着,大坝埂上有人急呼,传来爷爷已经去世的口信。大人们抱着我们往下一路狂奔,到时一屋子沉沉的哀哭。我在父亲的臂膀里,看见姐姐们都跪在地上,膝下垫着从大门上撕下来的红对子,床上有人给爷爷穿上黑色寿衣。我并不懂得害怕,只是觉得暗昏的灯泡下红对子的纸那么红,接着便被放下来,和姐姐跪在一起。那一年我五岁。
我们若去给爷爷上坟,跪拜之后,就一定会往山里走走,掐些映山红花来吃。我们的山上都是红土,下雨天时,红土为雨水浸泡,松软如糕,几不能行。这红土却适合种杉木,又自生自发出许多的映山红。“映山红”三个字念得快时,听起来就像是“焰山红”,有时我们又只叫它“大红花”,实在是简陋得厉害了。往二阿姨家的唐家村,路上经过一口清水塘,水塘边一个小坡,春天满山都是,我的理解“映山红”的意思,便是从这山坡的直观中得来。矮的有半人高,山路边处处皆有,几米高的大树,则多生在较深蔽的山中,蓬蓬一棵,花红飞溅,上山掐蕨禾时可以碰见。这时看惯满山花的我们,也要为对面绝处那一树花小小地惊叹一下。我们吃花,折一枝带嫩叶的枝子,将花摘下,掐去尾部,抽去花丝,穿到枝子上。如此穿了许多朵,成密密一枝花串,才放口大嚼,这样滋味比单吃一朵来得甘酸与好玩。也掐一点抱回去养,路上有时忍不住,又吃一点,直到看看再吃花就不好看了,才停下来。满山的映山红,那时看得何等平常的东西,殊不料如今竟年年春天想看一枝而不可得。城市花坛里春天常见紫色杜鹃,这杜鹃无由解我的相思,那样低矮、粗壮的枝叶,怎么抵得上一树映山红纤长舒展的枝子?映山红倩红的花,也远比紫色杜鹃清丽秀气。
清明里另一个我喜欢看的东西却是飘摇在田埂与坟头上的白纸幡,这喜好大约很古怪,在小时候的我,于是成一个秘密。最朴素的纸幡是老人亲手所剪,从小店里买来软薄的白纸,裁后折成几层约一米长两分宽的长条,用旧剪刀绞成波浪形状的连钱花纹,稍稍抖落开来,使之蓬松有姿,中间再用一两片朱红的纸片束起,顶端捻成细细的纸捻。路边或山边随处可见指头粗细的水竹与苦竹,这时用刀砍几枝来,擗净枝叶,只留顶端一枝分岔,将纸幡系上。纸幡理应插在坟头,地方风俗简陋,有的人家就随便在田埂角上一插,就算尽了一番孝心。那天田埂上到处可见一枝细竹挑着雪白轻软的纸幡,风时翩然而起,少年的心里于是也觉得它好看。这纸幡要经过许多雨打露侵,才慢慢碎成焦黄的断片,浸到田埂上的泥土里。很久以后,还会在一个田角上遇见光棱棱一枝已从翠绿褪作枯黄的竹枝。有时也有人家抬了箱笼,吹吹打打上山,多是去年的新丧,才有此番隆重。我远远看着,很喜欢那热闹,猜着箱子里大概是一碗昂着头的公鸡,一碗煮得干硬发生的米饭,上头插三枚香,香灰落到饭上。此外有整条的鱼,大块油腻的肥肉,都做得粗糙应付,不像给人吃的。心里忍不住怪,供都供了,怎么不做得好吃一些,坟里的人会喜欢那样的东西么?我但是爱看那种热闹罢了。我们自己上坟,只是买一挂小火炮,几刀三六裱纸,去坟头跪着烧掉,磕两个头,如此而已。我会把裱纸打成漂亮的扇形,这是跟父亲学的。也许父亲也曾在爷爷的坟头酹过白酒,此时我却不能肯定是否出自我的想象。有些年父亲还会带着锄头,锄一锄蔓延的荒草,看看坟前柏树的长势。爷爷坟前有一棵柏树,十多年过去,也只一人多高,有时结出奇形怪状的柏子,青果上覆薄薄一层白霜。那时我并不明白柏树后所隐藏的“松柏以识其坟”的意义,只当是为了好看。然而柏树又并不好看,不如山间许多的旧坟,无人祭扫,坟头爬满金樱子和野蔷薇,薰薰的太阳下开满水红与粉白的花。
事实上,一棵小小的、生长缓慢的柏树,远是守不住坟的。后来我们离开家乡,不过几年,我再去找爷爷的坟时,虽然记得那样真切,就在那一片山坡上,再走到时,眼前只是一片密实的野竹与荆棘,遮得人望不到边。人们不再常常进山砍柴,新修的公路也使得山路迅速被抛弃,这山坡连同通往山中的路,都已被刺笆笼堵得结结实实。我试图穿过荆棘去找,终究迷了路一般寻不着,连那棵柏树都不见踪影。我也就退出来,不再去找,知道以后父亲回来时,可以持刀砍出一条路来。即使爷爷的坟真的就此隐没在四面涌起的荆棘与野树中,他的坟上大概也是爬满金樱子与野蔷薇,一个普通人的结局,也许是这样彻底托体同山阿最好吧。
——摘自(豆瓣) |
|
| 2016-04-01 |
 |
|
|
| |
|
|
|
|